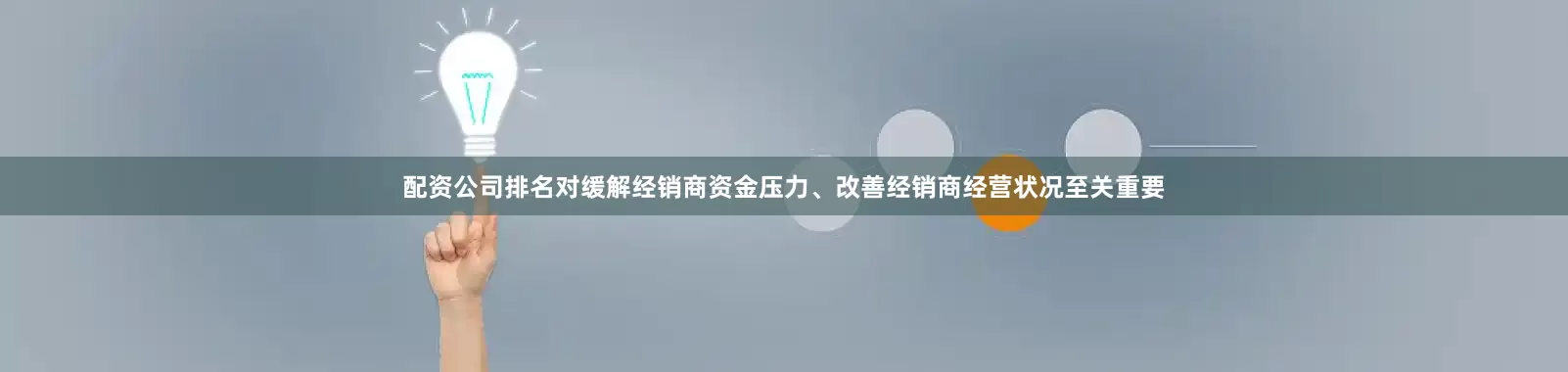自人民军队成立以来,无数功勋卓著、英勇善战的王牌部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第二野战军第12军堪称众多王牌军中的翘楚。

审视众多野战军的精锐之师,不难发现一个共同之处:它们的初任纵队司令,即军长,往往被授予上将军衔。
以第四野战军旗下第38军、第39军、第40军为例,三军军长李天佑、刘震及韩先楚均荣获上将军衔。
以第三野战军之第20军与第27军为鉴,叶飞与许世友两位将领均荣获上将军衔。
例如,第一野战军的精锐之师——第一军,其军长贺炳炎亦于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的崇高荣誉。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之时。”
全军对12军的奇异状况普遍感到困惑。首任军长王近山在众多将领中,以“闹衔”之盛闻名。这一情景甚至被搬上了荧屏,融入以他为主人公的电视剧《亮剑》之中。
12军的渊源可追溯至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该部成立于解放战争初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其初创阶段,以太行军区第六分区机关及其直属队为基石,随后逐步融入了韦杰支队、石志本支队、秦基伟支队以及向守志支队等力量。经过一番整编,第六纵队实现了正规化建设,下辖十六、十七、十八三个旅,总兵力达到1.3万人。
“纵有钢铁无数,亦需精神不竭。”装备或许粗陋,但精神之火绝不能熄灭。正因如此,六纵成为了一支精神力量充沛的部队。

1946年7月,被誉为“疯子司令员”的王近山接任六纵司令一职,而杜义德则被任命为政治委员。自红军时代起,王近山便以其“遇敌必交锋”的英勇形象而闻名于世。
杜义德,一位既充满战斗激情又具备卓越政治工作才能的勇猛将领。刘伯承曾对他给予极高的赞誉:
“杜义德身兼政委与司令双重职务,文韬武略,才识兼备。”
彼时,干部们的文化素养普遍较低,对于“文武双全”这一概念感到困惑。刘伯承便亲自予以阐释:“所谓‘文武双全’,即指既通文墨又擅武艺,既能领兵作战,亦能从事政治工作。”
除了司令员与政委之外,6纵下辖的三位旅长均声名显赫,无一不是赫赫有名之辈。16旅的指挥权暂由尤太忠接任,17旅则由李德生担任旅长,18旅的旅长一职则由肖永银执掌。
一时之间,第六纵队可谓是英才荟萃,将星璀璨。
王近山与杜义德,皆系浴血奋战、从尸山血海中脱颖而出的勇猛将领,对军事训练的必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王近山专注于训练工作,每当闲暇,便亲临部队一线,亲自传授士兵射击、投弹、爆破、刺杀及土工作业等五大技能,并指导夜战技巧。杜义德则着重于政治教育,以身作则。两人携手合作,使得第六纵队迅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随着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六纵部队迅速迎来了展示实力的关键时刻。1946年9月,刘峙、陈诚与白崇禧三位将领联手拟定作战策略,集结了三十万精锐之师,分兵两路,对我晋冀鲁豫根据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势。相较之下,刘邓大军所能调动的兵力不过五万。面对三十万的强敌,形势显得异常严峻,危机四伏。

刘伯承凝神细察地图,继而提出先集中兵力歼灭一路敌人的策略,目标锁定为孤立无援的整编第三师。该师在抗战时期曾参与滇缅公路对日作战,装备了部分美制武器,全师兵力逾14000人,下辖炮兵团、工兵营、通讯营和战车营。在中原突围的战斗中,整3师凭借战车的快速推进,对我军后卫部队造成了严重打击。尽管整3师并非我军五大主力之一,但其战斗力不容小觑。
关于谁将担任先锋,刘伯承心中尚存疑虑,这场战役无疑是一场艰难的硬战。一旦失利,部队的精英骨干恐将面临瓦解。在作战会议上,刘伯承期望能够有一位纵队司令主动挺身而出。然而,鉴于战斗的艰巨程度,所要面对的困难重重,一时间,众将皆陷入了沉默。
然而,正当此时,王近山霍地起身,主动请缨道:
“第六纵队就交给我们负责吧!经过与政委的商讨,我们这支纵队相较于二纵、三纵、七纵,显得更为年轻。将我们置于与敌人激战的前线,虽然充满挑战,但却是值得的。只要我们能够确保主力纵队的存续,晋冀鲁豫解放区便能够坚守阵地,最终赢得胜利。鉴于此,我们愿意迎难而上,投身于这场战斗!”
继此之后,王近山目光如炬,声音洪亮地宣誓道:
“尊敬的老师长、邓政委,今日王近山在此立下重誓:若不将赵锡田彻底剿灭,绝不归返与你们相见!我们第六纵队愿意接受最为艰巨的挑战,誓死奋战!即便纵队所剩仅一旅,我愿担当旅长,由杜义德同志担任旅政委;若战至仅余一团,我将成为团长,而老杜则出任团政委;若只剩下一个连队,我自当连长,老杜则担任指导员。纵队虽至尽灭,但问心无愧,既对得起党的培养,亦对得起养育我们的太行山上的父老乡亲!”
王近山此语一出,全场顿时陷入了震惊之中。就在此刻,杜义德猛地起身,犹如一座铁塔般矗立在王近山面前。他无需多言,仅需紧挨着王近山站立,便已足以表达其坚定支持之意。
刘邓两位首长素来不喜欢情绪激动,但听闻王近山所言,亦不禁情绪激昂。刘伯承猛地一挥右手,斩钉截铁地说道:“打!我全力支持你出兵!”

1946年9月7日,细雨绵绵,残酷的大杨湖战役就此拉开序幕。我军六纵以十八旅为先锋,对敌阵地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势。及至黎明时分,第59团的两个营已全部损失,我军亦承受了不小的伤亡。
敌军的战斗日志中如此感叹:“此次战役的残酷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六纵的装备远逊于整编第3师,然而在精神层面,我军却完全压制了敌军。战士们奋勇争先,连续发起冲锋,战场之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然而,最终六纵笑到了最后,整编第3师全军溃败,师长赵锡田亦沦为俘虏。
在这场激战中,年轻的六纵异军突起,一战成名,迅速跃升至中原野战军头等纵队的行列。六纵也深得首长刘伯承的厚爱,每逢遭遇恶战,必是六纵挺身而出。
然而,正当此刻,蒋军从东西南北三方对驻守在汝河南岸桥头堡的我军形成了包围之势,紧随其后的三个蒋军师团,与我军的距离亦不过一日之遥。敌军前堵后追,形势岌岌可危,危机程度前所未有。

彼时,王近山因病休养,代理指挥的重任落在了杜义德的肩上。他果断决策,命令肖永银率领的第十八旅担任先锋开路,尤太忠指挥的第十六旅殿后,以保护全军顺利渡河。开路和殿后,这两项任务尤为考验部队的战斗力和团结精神,因为它们都是艰难的硬仗,伤亡惨重。经过一天的激战,肖永银的第十八旅战士们将刺刀装上枪管,揭开了手榴弹的盖子,遇到敌人便勇猛迎战,攻克一个村庄后,又迅速转向下一个目标,最终硬生生开辟出一条血路。
执行阻击任务的十六旅承受了更为惨烈的考验,连长英勇牺牲,排长挺身而出,接过了指挥重任;班长亦壮烈捐躯,战士们纷纷上前填补空缺。当整个班级仅剩一名战士时,他孤军奋战,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经过一番激战,战场上布满了敌人的尸体。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在六纵的顽强拼搏下,中野指挥部和中原局机关终于成功渡过了汝河。然而,六纵在短短一夜之间付出了数千人的惨重代价,牺牲的战友们被集中埋葬,仅用毯子轻轻一卷,便归于尘土。
战后,尤太忠自豪地对记者说:
“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在大别山地区,主要依托的是第六纵队。他们曾与我们同住了一周。起初,他们与另一支部队并肩作战时,显得有些被动。后来,邓政委情绪激动地对我说:‘真是倒霉,我不想再跟他们同行了,我要和你们六纵一起走,和你们并肩作战’。”
“若欲寻觅刘邓大军,首要目标便是六纵。”

在随后的激战中,第六纵队屡建奇功。即便是敌方的国防档案,也不得不赞叹其卓越的战功。
“刘伯承部下辖之六纵队,由王近山担任司令员,杜义德出任政治委员,部队下辖三个旅:十六旅由尤太忠担任旅长,十七旅由李德生指挥,十八旅则由肖永银领导。这支纵队擅长攻坚作战,指挥艺术高超,纪律严明,在共军中被誉为主力纵队。”
1947年,王近山将军伤愈重返战场,率领部队参与了襄阳战役。他大胆创新,运用“刀劈三观”的巧妙战术。在这场战役中,李德生的第十七旅表现尤为出色。在极短的时间内,襄阳的险要地形被一一攻克,城门四开,守将康泽与郭勋祺亦被生擒。襄阳战役共歼敌逾两万人,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五路大捷之一。朱德元帅对此次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小型模范战役”。
在淮海战役的激战中,王近山与杜义德所率领的第六纵队,肩负着主攻的重任。面对装备精良、配备美式武器的黄维兵团,王近山及第六纵队毫不畏惧,他们与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紧密协作,于大王庄与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48年12月15日,夜幕低垂,月华初上,黄维兵团终于踏入了历史的幽暗深处。然而,这一次,王近山并未感受到大胜的欢愉,眼前是一片血海尸山,无数英勇的战士在沙场上英勇捐躯。一将功成万骨枯,王牌六纵所铸就的荣耀,背后却是战士们鲜红的血与无尽的牺牲。
在经历了三大战役的洗礼之后,中原野战军摇身一变,成为了第二野战军。王近山同志则受命担任了第三兵团的副司令员,同时兼任第12军的军长与政治委员之职。与此同时,杜义德同志被调配至第十军,开启了一段新的职业篇章,担任了军长一职。在第12军,肖永银同志担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原16旅更名成为34师,由尤太忠同志出任师长;17旅更名为35师,李德生同志担任师长;而原18旅则更名为36师,邢荣杰同志执掌师长之位。
继此,12军投身于渡江战役及解放大西南的征程。剿匪任务一结束,便即刻踏上征程,奔赴朝鲜,投身于抗美援朝的烽火之中。在上甘岭这一闻名遐迩的战役中,当战局进入高潮阶段,王近山将军下令,命李德生将军率领12军火速驰援前线,最终以辉煌的胜利载入史册。人皆知上甘岭有秦基伟将军的15军,却鲜有人知晓,12军才是真正发挥定海神针作用的英勇部队。
战争落幕之后,12军的将士们被派遣至全国各地担任新的职务,他们各展所长,均绽放出璀璨的光辉。真可谓,聚则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散则似漫天繁星,熠熠生辉。
归国之后,王近山先后担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以及军区顾问等职。

杜义德投身海军事业,曾历任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海军第二政治委员以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之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他担任了兰州军区司令员,并荣任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出人意料的是,在原12军的将领群体中,李德生的成就尤为卓越。1969年,当时年届五十三岁的李德生被周恩来总理亲自委以重任,调至中央任职,先后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达到了他人生事业的顶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尤太忠曾历任二十七军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以及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从其丰富的履历来看,尤太忠无疑是一位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
肖永银曾担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同时兼任南京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副司令员,以及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王近山与杜义德双双荣获中将军衔,然而6纵的“三剑客”——肖永银、李德生、尤太忠,却仅被授予少将军衔,未能有上将之列。
当1988年军衔制度得以恢复之际,尤太忠与李德生均荣获上将军衔,唯独肖永银未能如愿以偿,错过了这一荣誉。当有人就此提问时,肖永银却以轻松的语调,毫不在意地回应道:“我是那个落后的司令啊!”

更让人动容的,是12军将领间那份坚不可摧的友谊。他们不仅是上司与下属,战友与同伴,更是情同手足的至交好友。
王近山昔日因犯错,被降至农场劳动。他那往昔的部下们,心中始终挂念着他,对他的遭遇不曾忘怀,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1969年,时任27军军长的尤太忠向许世友提出请求,期望能促成王近山的复出。许世友对此表示赞同,并立即将此事禀报了毛主席。不久,王近山得以重返岗位,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当王近山抵达南京之际,尤太忠、肖永银、吴士宏三位军职干部特地前往火车站,热情地迎接他的到来。
王近山履新后,从职务层面来看,他的地位实则不及昔日同袍肖永银。尽管如此,王近山对他始终怀有敬意,习惯以“肖司令”尊称。然而,在肖永银的心目中,王近山始终是那位不可替代的“王司令”。
1973年,在一次与父亲王近山的闲谈中,女儿王媛媛不经意间提到了李德生的名字。然而,当“李德生”这三个字从她口中滑出,平易近人的王近山却突然怒火中烧,他猛地一拍桌子,愤然起身,厉声斥责起来:
"李德生不是你能随便叫的。"
1974年,李德生不期然地在邓公面前谈起了王近山的遭遇。开场白中,他不禁回忆起在六纵的岁月,随后又话题转向了当年那场激动人心的定陶之战。邓公听后,感慨万分。
在任何时期,我们都不能忘记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英勇奉献的同志们。据此,我已为他安排了在当前大会常委会的人选。经过中央的讨论,考虑到没有军队代表的席位,特将王近山同志任命为全国政协常委。

1978年,王近山将军不幸因癌症离世,肖永银将军悲痛欲绝,遂亲自挥毫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彼时,王近山将军担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之职。肖永银将军认为“副”字过于显眼,遂用笔将其轻轻圈去。
“人已故去,不宜再下命令安排仪式,就称作顾问即可。”这一变动颇具特殊意义,使得王近山的葬礼规格从正军级立刻提升至大军区正职级别。
正因如此,12军方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纵使12军的将领们已相继离世,革命先辈们所传承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依旧在中华大地的广袤土地上激荡飞扬。
盛鹏配资-股市配资开户加杠网-配资炒股流程-最新股票配资配资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